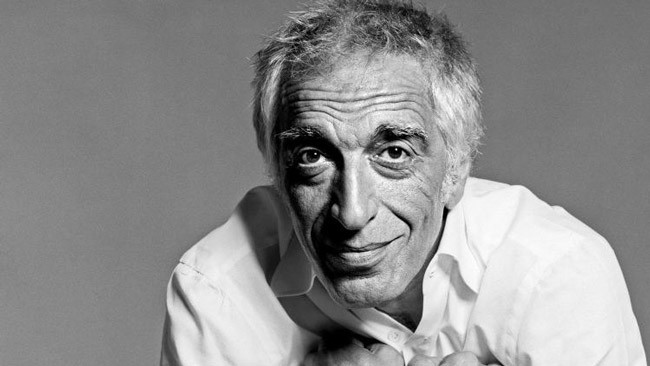随着特朗普抛弃民主价值观和盟友,完全依赖美国、拒绝并对抗中国不再是一条可行的前进道路。不首先确保和平,就不可能有民主。
郑志刚
■
9月上旬我有幸参见了一个以振兴科技教育为主题为期两周的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是来自工科背景的学者,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凤毛麟角。尽管与会者学科背景差异很大,但大家一个共同感兴趣的主题是如何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科技教育强国。这无疑是这次研讨会吸引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荣誉感的学者的缘由所在。邀请的与会的部分学者基于自身的科研教育经历和身边杰出团队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做了大量精彩的分享。其中涉及的科技精英,既包括已故的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邓稼先、于敏和汉字输入法的发明者北大方正创始人王选,和前不久离世的周光召,也包括目前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院士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公关项目的青年科学家。令每位与会者印象深刻的是,邓稼先和于敏这些优秀的科学家们在那样艰苦环境中通过科研坚守和集体协同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科技辉煌。
回顾过去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随着思考的深入,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聚焦到未来如何使中国成为科技教育强国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成为科技教育强国呢?
第一,从赶超式研究到创新式研究。
在邓稼先所处的那个时代,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的科学家必须以团队作战,攻坚克难,快速实现从无到有。目的仅仅是实现和主要国家在竞争策略选择上的相互制衡。那时的科研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别人有的,我们也应该有。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科学研究范式总结为赶超式研究。
毫无疑问,对于赶超式科研,采用大军团作战的科研攻关方式是适当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科研目标是明确的,清晰的。尤其是刚刚建国和经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可以水到渠成地把组织军队作战的经验复制到赶超式研究中。一方面是赶超式研究科研目标的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使大家容易和习惯接受大军团作战的研发组织模式。因而,在邓稼先那个时代,取得时至今日令世人瞩目的科研成就除了那一代科学家的艰辛付出,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时代的产物。强调这一点仅仅是为了表明它所具有的时代不可复制性。
而时至今日,科研的目标从以往的清晰变得模糊,谁都很难预测下一个科技热点是什么。记得比尔•盖茨最初并不看好的互联网,马云和马化腾同样不看好的云计算,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风靡全球,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新的时代。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当下引领科技风潮的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机构是以利益回报为目的企业方式组织起来的一个个研究机构,虽然他们无论自己还是别人有时都把他们称为“团队”。但这一团队与中国当年邓稼先领导和组织的(国家)团队不可同日而语。OpenAI在市场资本的支持下,美国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利用非营利的愿景和有效的组织构架,7年的时间让新一代人工智能ChatGPT横空出世。其间这些科研机构像绝大多数商业机构一样,发生过创始人面临被辞退威胁的治理危机,不断传出核心科研人员的离职和跳槽。但这并不影响作为科研机构OpenAI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引领。
与邓稼先时代赶超型研究不同,当今时代更多是创新型研究。如果简单归纳二者的区别,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以下方面存在严重差异。其一,前者服务国家战略,后者以企业盈利为目的;其二,前者科研目标明确,后者科研目标模糊;其三,前者以国家投资为主,后者以企业自己(项目吸引)筹集资金为主;其四,前者科研组织以国有机构为主,后者科研组织以私人机构为主。
第二,从团队式人才培养到个性化人才培养。
谈到科学研究,自然离不开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的培养。在这次研讨会上,一个被誉为最美教育团队的领头雁的一位院士闪亮登场。这位院士围绕人才培养做了大量工作,又是创作专业歌曲,组织所在学院的师生“授旗”,又是组织不同高校间学科研讨会,甚至在周末都在线上发起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公益讲座”,吸引大量青年学子开始热爱并积极投身这项目前并不那么时尚的科研方向。这位院士讲得声情并茂,绘声绘色,赢得了与会者阵阵掌声。
但在掌声之后,不少与会的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培养模式最好的结果是只能复制这位院士,出现该院士的No2,No3……更何况这位院士已经为该领域设置了天花板,后来者很难再超越他了。这些与会者的评论使我想起,在美国风险投资圈的一种IPO(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定价文化。如果一位创业者来自名校,很好,他创办企业的IPO定价会比非名校高很多;如果这位创业者不仅来自名校,而且有辍学经历,更好,他创办企业的定价会比名校背景的创业者创办的企业更高。在我们所熟知的科技明星中,有名校辍学经历的科技工作者大有人在,比尔•盖茨,阿尔特曼、马斯克等等俯首皆是。
而如今的科技竞争,中国固然需要类似该院士致力于培养的被称为“XX铁军”的整齐划一的科技工作者,也许我们更加需要的是马斯克,阿尔特曼式的充满个性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对科技发明充满想象力,不拘一格,但在生活中个性张扬,不拘小节,甚至在私生活中充满各种争议。一位与会者曾经分享了这样的观点,在包容同性恋等多元化的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将更加活跃。
第三,从以国家主导的科研项目申请的研发投入到以企业为中心吸引市场投资的研发投入。
如今在美国引领国际科技前沿无论是马斯克的Space-X,阿尔特曼的OpenAI,还是更早的苹果和微软,我们根本看不到国资的影子。在全球500强企业的榜单上我们不时看到这些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所谓“民企”的科技公司的身影。
在研讨过程中,一位学者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的国家科研机构在国家资金的支持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深海探测。一项新的突破是深海探测深度达到10000米,这使中国成为唯一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这位学者无意中提及其实中国南海海底平均深度只有3000-4000米。而为了完成这项研究的测试,我们还需要远赴深度可达70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我注意到,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多与会的学者都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研发出这样的产品,研发者也许会不出意料地拿到某项国家大奖。然而,脱离了市场的实际需要,不计成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仅仅为了赶超,为了科研而科研,这样赶超型科研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看到这种长期科技落后形成的赶超型科研思维的可怕之处。在中国科技历史上已经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而可以预料的是,在未来很长的时间中国仍将继续在为此付出代价。
作为对照,我注意到,在美国科技界出现了一种我所谓的“成本节省型创新”。向太空发射载人航空器不是一项新的发明,但马斯克领导的Space-X这家中国人眼中的“民企”却致力于发射装置的可回收,和原来一枚火箭只发射一颗卫星,现在一枚火箭同时发射N颗卫星。马斯克这样做也许最初的目的就是作为一家民企为了实现盈利目的,当然需要节省成本,然而却带来重大的科技创新。这显然不同于“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的国资投入。更何况全球科学界都在呼吁,要对科学研究采取包容态度,允许失败。国资不计成本地投入不仅缺乏来自盈利目的的资本的约束,而且受到普遍奉行的科研创新失败包容文化的原谅,可以想象的是,在上述科研效率下,中国利用有限的资源形成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技产出将少得可怜。
同样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北大王选团队的亲历者的分享给我带来两个方面的震撼。其一是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在艰苦环境中按照自己意愿特立独行、持之以恒、努力前行的科学工作者。王选在文革期间为了提高英语长期坚持收听当时所谓的敌台BBC,一度为此被怀疑间谍,长时间接受审查学习。这为从未在国外接受系统教育的王选后来便捷地阅读国外的科学技术文献,发明汉字激光拍照系统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其二是王选亲手创办的北大方正在几年前遭到破产重整。我在想,中国有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也许并不难,难在出现一家好的企业以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使这种产品落地,难在形成一种好的企业制度让一家企业基业长青。我们光想到科技大力投入,光想到举国体制,但没有很好的企业发展生态支持的高的科研效率,很多类似方正的好的项目也无以为继。听了那么多国内一流学者分享的前沿科技成果,我的内心没有感到丝毫欣喜和快慰,我的内心却比任何时候都沉重起来。我感到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经济学者肩上的重任。
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科技教育强国呢?概括而言,我们在研究动机上需要主动摆脱赶超式研究的惯性思维,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研发;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我们要从注重团队式人才培养到包容和鼓励个性化人才培养;在科研投入方式上,从以科研项目的研发投入到以企业为中心吸引市场资金风险投资的研发投入。也许有一天,中国有了大量企业主导的创新型研究,大量类似(没有头衔,也没有国家基金项目支持的)马斯克、阿尔特曼式的科技工作者在中国集中涌现,中国就离真正的科技教育强国不远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读者评论
MORE +
热门排行榜
OR
+
郑志刚
■
9月上旬我有幸参见了一个以振兴科技教育为主题为期两周的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是来自工科背景的学者,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凤毛麟角。尽管与会者学科背景差异很大,但大家一个共同感兴趣的主题是如何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科技教育强国。这无疑是这次研讨会吸引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荣誉感的学者的缘由所在。邀请的与会的部分学者基于自身的科研教育经历和身边杰出团队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做了大量精彩的分享。其中涉及的科技精英,既包括已故的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邓稼先、于敏和汉字输入法的发明者北大方正创始人王选,和前不久离世的周光召,也包括目前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院士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公关项目的青年科学家。令每位与会者印象深刻的是,邓稼先和于敏这些优秀的科学家们在那样艰苦环境中通过科研坚守和集体协同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科技辉煌。
回顾过去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随着思考的深入,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聚焦到未来如何使中国成为科技教育强国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成为科技教育强国呢?
第一,从赶超式研究到创新式研究。
在邓稼先所处的那个时代,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的科学家必须以团队作战,攻坚克难,快速实现从无到有。目的仅仅是实现和主要国家在竞争策略选择上的相互制衡。那时的科研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别人有的,我们也应该有。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科学研究范式总结为赶超式研究。
毫无疑问,对于赶超式科研,采用大军团作战的科研攻关方式是适当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科研目标是明确的,清晰的。尤其是刚刚建国和经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可以水到渠成地把组织军队作战的经验复制到赶超式研究中。一方面是赶超式研究科研目标的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使大家容易和习惯接受大军团作战的研发组织模式。因而,在邓稼先那个时代,取得时至今日令世人瞩目的科研成就除了那一代科学家的艰辛付出,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时代的产物。强调这一点仅仅是为了表明它所具有的时代不可复制性。
而时至今日,科研的目标从以往的清晰变得模糊,谁都很难预测下一个科技热点是什么。记得比尔•盖茨最初并不看好的互联网,马云和马化腾同样不看好的云计算,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风靡全球,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新的时代。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当下引领科技风潮的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机构是以利益回报为目的企业方式组织起来的一个个研究机构,虽然他们无论自己还是别人有时都把他们称为“团队”。但这一团队与中国当年邓稼先领导和组织的(国家)团队不可同日而语。OpenAI在市场资本的支持下,美国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利用非营利的愿景和有效的组织构架,7年的时间让新一代人工智能ChatGPT横空出世。其间这些科研机构像绝大多数商业机构一样,发生过创始人面临被辞退威胁的治理危机,不断传出核心科研人员的离职和跳槽。但这并不影响作为科研机构OpenAI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引领。
与邓稼先时代赶超型研究不同,当今时代更多是创新型研究。如果简单归纳二者的区别,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以下方面存在严重差异。其一,前者服务国家战略,后者以企业盈利为目的;其二,前者科研目标明确,后者科研目标模糊;其三,前者以国家投资为主,后者以企业自己(项目吸引)筹集资金为主;其四,前者科研组织以国有机构为主,后者科研组织以私人机构为主。
第二,从团队式人才培养到个性化人才培养。
谈到科学研究,自然离不开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的培养。在这次研讨会上,一个被誉为最美教育团队的领头雁的一位院士闪亮登场。这位院士围绕人才培养做了大量工作,又是创作专业歌曲,组织所在学院的师生“授旗”,又是组织不同高校间学科研讨会,甚至在周末都在线上发起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公益讲座”,吸引大量青年学子开始热爱并积极投身这项目前并不那么时尚的科研方向。这位院士讲得声情并茂,绘声绘色,赢得了与会者阵阵掌声。
但在掌声之后,不少与会的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培养模式最好的结果是只能复制这位院士,出现该院士的No2,No3……更何况这位院士已经为该领域设置了天花板,后来者很难再超越他了。这些与会者的评论使我想起,在美国风险投资圈的一种IPO(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定价文化。如果一位创业者来自名校,很好,他创办企业的IPO定价会比非名校高很多;如果这位创业者不仅来自名校,而且有辍学经历,更好,他创办企业的定价会比名校背景的创业者创办的企业更高。在我们所熟知的科技明星中,有名校辍学经历的科技工作者大有人在,比尔•盖茨,阿尔特曼、马斯克等等俯首皆是。
而如今的科技竞争,中国固然需要类似该院士致力于培养的被称为“XX铁军”的整齐划一的科技工作者,也许我们更加需要的是马斯克,阿尔特曼式的充满个性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对科技发明充满想象力,不拘一格,但在生活中个性张扬,不拘小节,甚至在私生活中充满各种争议。一位与会者曾经分享了这样的观点,在包容同性恋等多元化的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将更加活跃。
第三,从以国家主导的科研项目申请的研发投入到以企业为中心吸引市场投资的研发投入。
如今在美国引领国际科技前沿无论是马斯克的Space-X,阿尔特曼的OpenAI,还是更早的苹果和微软,我们根本看不到国资的影子。在全球500强企业的榜单上我们不时看到这些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所谓“民企”的科技公司的身影。
在研讨过程中,一位学者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的国家科研机构在国家资金的支持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深海探测。一项新的突破是深海探测深度达到10000米,这使中国成为唯一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这位学者无意中提及其实中国南海海底平均深度只有3000-4000米。而为了完成这项研究的测试,我们还需要远赴深度可达70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我注意到,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多与会的学者都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研发出这样的产品,研发者也许会不出意料地拿到某项国家大奖。然而,脱离了市场的实际需要,不计成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仅仅为了赶超,为了科研而科研,这样赶超型科研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看到这种长期科技落后形成的赶超型科研思维的可怕之处。在中国科技历史上已经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而可以预料的是,在未来很长的时间中国仍将继续在为此付出代价。
作为对照,我注意到,在美国科技界出现了一种我所谓的“成本节省型创新”。向太空发射载人航空器不是一项新的发明,但马斯克领导的Space-X这家中国人眼中的“民企”却致力于发射装置的可回收,和原来一枚火箭只发射一颗卫星,现在一枚火箭同时发射N颗卫星。马斯克这样做也许最初的目的就是作为一家民企为了实现盈利目的,当然需要节省成本,然而却带来重大的科技创新。这显然不同于“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的国资投入。更何况全球科学界都在呼吁,要对科学研究采取包容态度,允许失败。国资不计成本地投入不仅缺乏来自盈利目的的资本的约束,而且受到普遍奉行的科研创新失败包容文化的原谅,可以想象的是,在上述科研效率下,中国利用有限的资源形成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技产出将少得可怜。
同样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北大王选团队的亲历者的分享给我带来两个方面的震撼。其一是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在艰苦环境中按照自己意愿特立独行、持之以恒、努力前行的科学工作者。王选在文革期间为了提高英语长期坚持收听当时所谓的敌台BBC,一度为此被怀疑间谍,长时间接受审查学习。这为从未在国外接受系统教育的王选后来便捷地阅读国外的科学技术文献,发明汉字激光拍照系统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其二是王选亲手创办的北大方正在几年前遭到破产重整。我在想,中国有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也许并不难,难在出现一家好的企业以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使这种产品落地,难在形成一种好的企业制度让一家企业基业长青。我们光想到科技大力投入,光想到举国体制,但没有很好的企业发展生态支持的高的科研效率,很多类似方正的好的项目也无以为继。听了那么多国内一流学者分享的前沿科技成果,我的内心没有感到丝毫欣喜和快慰,我的内心却比任何时候都沉重起来。我感到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经济学者肩上的重任。
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科技教育强国呢?概括而言,我们在研究动机上需要主动摆脱赶超式研究的惯性思维,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研发;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我们要从注重团队式人才培养到包容和鼓励个性化人才培养;在科研投入方式上,从以科研项目的研发投入到以企业为中心吸引市场资金风险投资的研发投入。也许有一天,中国有了大量企业主导的创新型研究,大量类似(没有头衔,也没有国家基金项目支持的)马斯克、阿尔特曼式的科技工作者在中国集中涌现,中国就离真正的科技教育强国不远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读者评论OR+ 更多
读者评论
OR
+ 更多
分享:
每日头条
OR
+
最新资讯
OR
+
热门排行榜
OR
+
OR品牌理念
+
■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OR 新媒体是一个提供时政、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资讯的平台,旨在为用户提供优质的阅读体验。网站的网址是oror.vip,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在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手机访问。.......